道艺并重:汤显祖的诗学取向
 222
222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和阳明心学的流行,重视个体价值、寻求思想解放、超越传统道德规范的自然人性论逐步成为晚明思想界的一股潮流,其中又以王学左派的“泰州学派”即“狂禅派”最称典型(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汤显祖少从“泰州学派”罗汝芳游,也是李贽学说的崇拜者(《答管东溟》),深受王学左派影响。他肯定人在天地中的地位,以为“天地之性人为贵”(《贵生书院说》),视“天机”“天性”与“人心”为一,以“人心”为本探求“天道”(《阴符经解》),追求精神自足。因此,他始终以“伉壮不阿之气”应对世间事,即便因此而屡遭挫折,“然终不能消此真气”(《答余中宇先生》)。以此为思想基础,他提出了“性乎天机,情乎物际”“含星吐激,自然而调”(《答马仲良》)的理论命题,且形成了至情文学观,既以“至情”论戏曲,亦以“至情”论诗,称“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耳伯麻姑游诗序》),又称“情致所极,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终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诗歌、序记、词辩之间。固圣贤之所不能遗,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调象庵集序》)。那么,汤显祖以情论诗,是否有悖于儒家道义呢?
王汎森在《明末清初的一种道德严格主义》中指出:“在主张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家的作品中,常能见到极为深刻的道德严格主义。这种现象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为特别突出。”姑且不论汤显祖是否也有“道德严格主义”的倾向,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作为士人,他虽然追求自然人性,但并未能摆脱儒家道义精神的影响。其《明复说》有言:“天命之成为性,继之者善也。显诸仁,藏诸用,于用处密藏,于仁中显露。仁如果仁,显诸仁,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生生之谓易’也。不生不易。天地神气,日夜无隙。吾与有生,俱在浩然之内……吾人集义勿害生,是率性而已。”如前所述,汤显祖视“天性”“天机”“人心”为一,在此又以“善”“仁”“用”相规约,强调“生生”之“仁”,追求明心以致用。同时,他勾连“道”与“法”解读“人心”与“天下”,强调仁道法度对性情的约束,在《云声阁草序》中说:“天下之物,最大者无如道与法。希微渊沦,憭恍浡郁,道之存也。劖错莹荡,方俨员幅,法之持也。法与道际,可以言心,可以言天下。心与天下,道法之所营也。性命功实节烈名誉之士,无一不在乎是。”其《君子戒慎》所说“君子率性,有不离之功焉。夫道合于性体,而每于动机失之也。君子岂能一息离欤。且道于性自相依附,人于道容有合离,则未有以定性而知诱之也”,《戈说序》所说“今昔异时,行于其时者三:理尔,势尔,情尔。以此乘天下之吉凶,决万物之成毁。作者以效其为,而言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睡庵文集序》所说“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都是以情说法,却大多涵容了深厚的道义精神。要而言之,“自然人性”与“道德严格”共存,其实也是汤显祖思想特点所在,这反映在诗学上则是道艺并重,极见复归风雅之气度。
一是言情而不悖于理。如其《义墨斋近稿序》,以“大雅”规范诗人超脱通达的情感表现,视“超然濬然,归于大雅”为“达者”,尽显道义之氤氲,大有调和情理之意味。又如对朱明之文士,汤显祖尤重宋濂,甚至于《答张梦泽》中给出“我朝文字,宋学士而止”的判断。实际上,宋濂诗学思想“显示出原道教化与抒写自我的双重特征,是重理与重文的融合,是政教与审美的兼顾”(左东岭《论宋濂的诗学思想》),以宋氏为尚,这也恰恰反映汤之诗学旨趣,终不离“发乎情,止乎礼义”之影响。再如,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言:“文长自负高一世,少所许可,独注意汤义仍,寄诗与订交,推重甚至,汤时犹在公车也。余后遇汤,问:‘文长文价何似?’汤亦称赏,而口多微辞。盖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汤于徐渭之态度,前后扞格,何以如此?其实,这也可于言情而不悖于理的诗学主张中寻找答案。大致而言,徐、汤两人虽有诗主情真而趋同的一面,但于性情与义理关系的认识,则多少存在隔阂。徐渭恃才负气,论诗主乎情,“其为诗若文,往往深于法而略于貌”(陶望龄《徐文长三集序》),过分强调一己之情的宣泄,于义理的重视则显不足。显然,这是汤显祖无法接受的。
二是重视诗之社会功用。汤显祖在《金竹山房诗序》说:“诗者,风而已矣……江以西有诗,而吴人厌其理致。吴有诗,江以西厌其风流。予谓此两者好而不可厌,亦各其风然,不可强而轻重也。立言者能一其风,足以有行于天下。若夫金右辰之诗,有不止一其风,而兼两者以究焉……故其诗旁魄愤发,幽缭致属,则大鄣之气也。标贯玄微,该验条传,则又非若吴人之风露自赏者。两者之风,较然粲然矣。得一为美好,而况其兼焉而不专者乎。”在此,他重申了言情不悖于理的意见,对“理致”“风流”的不同艺术表现未作轩轾之论,且大有统合两者之意愿;同时,又以“风”定义诗,阐发“兴观群怨”之旨,强调诗之社会功用。其《骚苑笙簧序》,称《离骚》兼有《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点,乃“有道者之言也”,这与《金竹山房诗序》的旨趣实相侔,亦显现会通“理致”“风流”以推阐诗之现实批判价值的取向。其《诗云缗蛮》,虽为制艺之作,但其所说“大贤觉人知止,因示以圣人之知止焉。夫人心之知诚宜用之于止矣,而不知圣人之知止,则亦何以缉其熙而敬之哉。且明德至善,即在家国天下伦理之间,而匪敬不止,匪知则明德不绍,而无所以一其敬也。是故咏《缗蛮》之诗,察丘隅之止也”,乃关联“家国天下”与“丘隅”,统论诗歌创作的原动力和目的,弘扬诗之事功价值的意趣亦见明了。
三是肯定“温柔敦厚”之诗教。汤显祖在《太平山房集序》中指出:“中庸者,天机也,仁也。去仁则其智不清,智不清则天机不神……绪为诗歌,漻然以和。”以“天机”和“仁”释“中庸”,又以“中庸”为关捩,论说诗歌创作当以平和醇厚为美,从风格的层面肯定“温柔敦厚”的诗教。其《明德先生诗歌集序》,高度评价罗汝芳之诗:“所至若元和之条昶,流风穆羽,若乐之出于虚而满于自然也,已而瑟然明以清……今之世诵其诗,知其厚以柔。”这同样展示了其以雅正为规范的基本审美态度。又其《与幼晋宗侯》一文,则是借明初吴中“高、张、杨、徐”四家诗之“一过已快。都有矩格,缊藉深稳,不漫作,大是以清气英骨为主”,贬抑“后辈李粗何弱”,既表达了对明代复古派的不满,也显示了维护“温柔敦厚”诗教的坚定立场。至于其《如兰一集序》所说“诗乎,机与禅言通,趣与游道合。禅在根尘之外,游在伶党之中。要皆以若有若无为美。通乎此者,风雅之事可得而言”,则是绾合“禅”“游”论“诗”,既联通内外,又着眼于虚实评价诗之美,不惟见歌者之灵心妙悟,亦展示了对现实的审美体悟,其守护和推阐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用心,同样清晰。
总的看来,汤显祖不仅重视情感于诗之基础作用,也未曾放弃对儒家道义的追求。岳元声《汤临川玉茗堂绝句序》曰“诗,六经之微言也。骚人好谭诗矣,谭诗好谭微矣。好谭微而微绝,亦复更为不好谭微矣。谭其所不好谭微,而微更绝。微言不续,情性淆讹,而天地万物之心闭。彼夫藉口雅言,而流连于鸟兽草木之骚屑者,此政不可与临川言诗者也”,关联“微言”“性情”论“玉茗堂诗”之隐喻,分析其道艺并重的诗学内涵,可以说是切中肯綮的。相反,大概是因为过分地强调汤显祖的“至情”论,以往一些研究有意无意地轻忽了其诗学言说中的道义关切,这与其论诗的本意自是隔了一层。
(作者:温世亮,系汕头大学文学院教授)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 
- 评论
- 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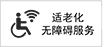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第一时间为您推送权威资讯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报道全球 传播中国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
关注人民网,传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