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走進去”還是“走出來”
在人工智能技術日新月異之際,人文教育問題再度被提上重要日程。回溯人類學科史,人文教育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邊緣地帶。隨著知識的迅猛增長,人類的科技理性一直在進步,但科學與人文的緊張、知識與文化的糾纏,始終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命題。要辨析和解決這個問題,最終還是要回到知識與文化的屬性及其關系上來。
人文教育涵括了“兩種知識”
作為近年來知識史領域的代表人物,彼得·伯克將知識界定為“與世界發生關系的任何形式”的“智慧”,大有將“文化”納入知識范疇的意味。而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德謨克利特認為存在“兩種知識,一種是真正的知識,另一種是模糊不清的知識。色、聲、香、味、觸都屬於模糊不清的知識”﹔思想家亞裡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則對人類以靈魂把握真理“能力”給出五條路徑,對知識與文化的范疇進行了寬泛界定,使得二者的屬性分野大致有了一個“物事”與“人事”的對應。
循此思路,知識以求真、求實為導向,是硬的“理”,是可以援以為用的“術”﹔文化以求善、求美為訴求,是軟的“道”,比起知識的具體性和應用性,文化具有抽象性和泛指性。無論是《周易》中“一陰一陽”的“道”說,還是《庄子》裡“道術將為天下裂”的預言,都不乏知識與文化分屬的教諭。進一步說,人類常常面臨這樣一個難題:在無常而強大的自然面前,人類顯得如此脆弱、無知、渺小﹔在“冷酷無情”之“硬的理”面前,求善、求美之“軟的道”何以著陸?為此,才有學者鍥而不舍地追問:面向蒼天,微渺如“一粒塵土”的我們如何鼓足勇氣做自己?這是以倫理道德為尺度的文化之問,更是尋求知識與文化同題共答的人文之問,也是技術革命之下的教育之問。
人文教育立足於“兩種文化”
古希臘時期,著名的柏拉圖學園曾挂出招牌“不懂幾何者不得入內”。這是一個典型的例証——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西方文明史表明,該時期,以科學、理性為主題的“知識”如日中天,尤其是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登上歷史舞台中心后,以文化、人文、社會為主體的語文學科連帶人文教育便棲居角落。面對此種情形,意大利學者維柯於18世紀以一種人文自信、社會科學自信的姿態向(自然)科學宣戰,其舉出的“義旗”為與知識、理性、智慧針鋒相對的撒手锏:“詩性智慧”。對此,我們可以稱之為前智慧,是在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原始、想象與詩性中尋覓人類文明的線索。
20世紀50年代,英國學者C.P.斯諾在他的《兩種文化》中,把“貧國”與“富國”並置,聚焦“科學家”和“文學知識分子”兩個群體,將雙方特有的“分量”“成就”做了分析,劃出了“科學家”和“文學家”之間的鴻溝,以此來論述“兩種文化”的不同屬性。他將兩種文化概括為“智力的發展”與“心靈的發展”:“坦率地說,任何一種文化,無論它是文學文化還是科學文化,都只能稱之為子文化。‘表征人性的本質和才能’,對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對思維的符號系統的應用,這才是最珍貴、最人性的兩種人類本性。”斯諾敏銳地感受到了超越“兩種文化”歧義及其對峙的“人文”的可能性,提出了以人文為背書的文化發展路徑,可惜,其思想只是一閃而過。
人文教育兼有兩種屬性
從知識與文化的內涵屬性看,前者屬“一”、后者屬“多”。“一”說的是知識的客觀性、規律性、普遍性,有著相對的恆定性、穩定性與確定性,這也正是將知識、理性與科學相提並論的原因﹔“多”意指文化的多元性和不確定性,是人類經驗、習俗、觀念的積累和添加,帶有顯著的地區、民族或國家之本土化屬性,其主觀性、歷時性、社會性一目了然。人文一方面有真理性(確定性),另一方面又要有人之主體性參與,因此具有善與美的非固定性,也就是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性為人文性留下了價值和意義空間,以“人”的尊嚴、靈魂、位格等涵化呈現作為主體來完成。這就構成了確定與不確定的緊張。也唯有這種緊張,促成了作為良知方向的人文教育屬性。
一方面,人文教育是價值涵養。價值涵養以知識為前提條件,沒有知識的長進,就難以有人文的充要。人文教育首先要說的是符合真理、事實的話,這樣的話才是人話。另一方面,人文教育是厚積薄發。人文之厚重,是從文化積累意義上而言,在此基礎上,教育以善和美作為和諧因子,既要確保硬性的客觀、科學,又要兼顧軟性的主觀、人情。
人文教育中的文化與知識不存在誰主導誰的問題。知識對於人類認識自然、把控自然是必需、必要的,但隻有知識與文化融通的人文良知,才是方向。人的道德觀、價值觀和人類知識生產總是處於互構當中,文化扮演著引領角色,在人文教育的方向意義上,知識和文化乃是驅動良知生成的舟車之兩輪。
人文教育在知識與文化的統一中走向通途
今天我們常講“培根鑄魂”,從某種意義上說,知識是根,文化是魂。在新的語境下,我們以科學理性作為支援,但不是“走進去”並消失在知識的浩瀚海洋之中,而是要“走出來”保有清醒的認知和自覺。人文教育提倡科學理性,一方面自然科學幫助我們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另一方面,人文科學在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尋求價值意義與社會秩序,強調對生命的尊重與呵護。比如對體弱者的同情,對婦女兒童的關照等。唯其如此,兩種“文化”或“知識”才能鑿枘互補,將道阻且長的“天塹”變成“通途”。這個“通途”是大道,也是正道。
古往今來,關於人文教育一向存在著是將知識最大化還是將文化最大化的觀念沖突。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一種“內卷”的思維范式在作祟:文化走進科學,從而獲得平起平坐的顯赫位格是一種進路﹔文化跳出知識的藩籬自成一統,則是另一種進路。然而,人類文明的發展告訴我們,“走進”還是“走出”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抉擇。知識作為工具、手段、路徑,是改善人類環境的重要支援,如何運用是關鍵﹔文化作為人類文明的重要來源,有“精華”和“糟粕”之分,因此如何最大程度地讓自己的文化被文明納入其中才是根本。
(作者:張寶明,系河南大學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院長、教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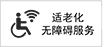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