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藝並重:湯顯祖的詩學取向
 222
222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的壯大和陽明心學的流行,重視個體價值、尋求思想解放、超越傳統道德規范的自然人性論逐步成為晚明思想界的一股潮流,其中又以王學左派的“泰州學派”即“狂禪派”最稱典型(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論》)。湯顯祖少從“泰州學派”羅汝芳游,也是李贄學說的崇拜者(《答管東溟》),深受王學左派影響。他肯定人在天地中的地位,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貴生書院說》),視“天機”“天性”與“人心”為一,以“人心”為本探求“天道”(《陰符經解》),追求精神自足。因此,他始終以“伉壯不阿之氣”應對世間事,即便因此而屢遭挫折,“然終不能消此真氣”(《答余中宇先生》)。以此為思想基礎,他提出了“性乎天機,情乎物際”“含星吐激,自然而調”(《答馬仲良》)的理論命題,且形成了至情文學觀,既以“至情”論戲曲,亦以“至情”論詩,稱“世總為情,情生詩歌,而行於神……其詩之傳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無所至,而必曰傳者,亦世所不許也”(《耳伯麻姑游詩序》),又稱“情致所極,可以事道,可以忘言,而終有所不可忘者,存乎詩歌、序記、詞辯之間。固聖賢之所不能遺,而英雄之所不能晦也”(《調象庵集序》)。那麼,湯顯祖以情論詩,是否有悖於儒家道義呢?
王汎森在《明末清初的一種道德嚴格主義》中指出:“在主張自然人性論的思想家的作品中,常能見到極為深刻的道德嚴格主義。這種現象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為特別突出。”姑且不論湯顯祖是否也有“道德嚴格主義”的傾向,然而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作為士人,他雖然追求自然人性,但並未能擺脫儒家道義精神的影響。其《明復說》有言:“天命之成為性,繼之者善也。顯諸仁,藏諸用,於用處密藏,於仁中顯露。仁如果仁,顯諸仁,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生生之謂易’也。不生不易。天地神氣,日夜無隙。吾與有生,俱在浩然之內……吾人集義勿害生,是率性而已。”如前所述,湯顯祖視“天性”“天機”“人心”為一,在此又以“善”“仁”“用”相規約,強調“生生”之“仁”,追求明心以致用。同時,他勾連“道”與“法”解讀“人心”與“天下”,強調仁道法度對性情的約束,在《雲聲閣草序》中說:“天下之物,最大者無如道與法。希微淵淪,憭恍浡郁,道之存也。劖錯瑩蕩,方儼員幅,法之持也。法與道際,可以言心,可以言天下。心與天下,道法之所營也。性命功實節烈名譽之士,無一不在乎是。”其《君子戒慎》所說“君子率性,有不離之功焉。夫道合於性體,而每於動機失之也。君子豈能一息離歟。且道於性自相依附,人於道容有合離,則未有以定性而知誘之也”,《戈說序》所說“今昔異時,行於其時者三:理爾,勢爾,情爾。以此乘天下之吉凶,決萬物之成毀。作者以效其為,而言者以立其辨,皆是物也”,《睡庵文集序》所說“道心之人,必具智骨﹔具智骨者,必有深情”,都是以情說法,卻大多涵容了深厚的道義精神。要而言之,“自然人性”與“道德嚴格”共存,其實也是湯顯祖思想特點所在,這反映在詩學上則是道藝並重,極見復歸風雅之氣度。
一是言情而不悖於理。如其《義墨齋近稿序》,以“大雅”規范詩人超脫通達的情感表現,視“超然濬然,歸於大雅”為“達者”,盡顯道義之氤氳,大有調和情理之意味。又如對朱明之文士,湯顯祖尤重宋濂,甚至於《答張夢澤》中給出“我朝文字,宋學士而止”的判斷。實際上,宋濂詩學思想“顯示出原道教化與抒寫自我的雙重特征,是重理與重文的融合,是政教與審美的兼顧”(左東嶺《論宋濂的詩學思想》),以宋氏為尚,這也恰恰反映湯之詩學旨趣,終不離“發乎情,止乎禮義”之影響。再如,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有言:“文長自負高一世,少所許可,獨注意湯義仍,寄詩與訂交,推重甚至,湯時猶在公車也。余后遇湯,問:‘文長文價何似?’湯亦稱賞,而口多微辭。蓋義仍方欲掃空王、李,又何有於文長。”湯於徐渭之態度,前后扞格,何以如此?其實,這也可於言情而不悖於理的詩學主張中尋找答案。大致而言,徐、湯兩人雖有詩主情真而趨同的一面,但於性情與義理關系的認識,則多少存在隔閡。徐渭恃才負氣,論詩主乎情,“其為詩若文,往往深於法而略於貌”(陶望齡《徐文長三集序》),過分強調一己之情的宣泄,於義理的重視則顯不足。顯然,這是湯顯祖無法接受的。
二是重視詩之社會功用。湯顯祖在《金竹山房詩序》說:“詩者,風而已矣……江以西有詩,而吳人厭其理致。吳有詩,江以西厭其風流。予謂此兩者好而不可厭,亦各其風然,不可強而輕重也。立言者能一其風,足以有行於天下。若夫金右辰之詩,有不止一其風,而兼兩者以究焉……故其詩旁魄憤發,幽繚致屬,則大鄣之氣也。標貫玄微,該驗條傳,則又非若吳人之風露自賞者。兩者之風,較然粲然矣。得一為美好,而況其兼焉而不專者乎。”在此,他重申了言情不悖於理的意見,對“理致”“風流”的不同藝術表現未作軒輊之論,且大有統合兩者之意願﹔同時,又以“風”定義詩,闡發“興觀群怨”之旨,強調詩之社會功用。其《騷苑笙簧序》,稱《離騷》兼有《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的特點,乃“有道者之言也”,這與《金竹山房詩序》的旨趣實相侔,亦顯現會通“理致”“風流”以推闡詩之現實批判價值的取向。其《詩雲緡蠻》,雖為制藝之作,但其所說“大賢覺人知止,因示以聖人之知止焉。夫人心之知誠宜用之於止矣,而不知聖人之知止,則亦何以緝其熙而敬之哉。且明德至善,即在家國天下倫理之間,而匪敬不止,匪知則明德不紹,而無所以一其敬也。是故詠《緡蠻》之詩,察丘隅之止也”,乃關聯“家國天下”與“丘隅”,統論詩歌創作的原動力和目的,弘揚詩之事功價值的意趣亦見明了。
三是肯定“溫柔敦厚”之詩教。湯顯祖在《太平山房集序》中指出:“中庸者,天機也,仁也。去仁則其智不清,智不清則天機不神……緒為詩歌,漻然以和。”以“天機”和“仁”釋“中庸”,又以“中庸”為關捩,論說詩歌創作當以平和醇厚為美,從風格的層面肯定“溫柔敦厚”的詩教。其《明德先生詩歌集序》,高度評價羅汝芳之詩:“所至若元和之條昶,流風穆羽,若樂之出於虛而滿於自然也,已而瑟然明以清……今之世誦其詩,知其厚以柔。”這同樣展示了其以雅正為規范的基本審美態度。又其《與幼晉宗侯》一文,則是借明初吳中“高、張、楊、徐”四家詩之“一過已快。都有矩格,缊藉深穩,不漫作,大是以清氣英骨為主”,貶抑“后輩李粗何弱”,既表達了對明代復古派的不滿,也顯示了維護“溫柔敦厚”詩教的堅定立場。至於其《如蘭一集序》所說“詩乎,機與禪言通,趣與游道合。禪在根塵之外,游在伶黨之中。要皆以若有若無為美。通乎此者,風雅之事可得而言”,則是綰合“禪”“游”論“詩”,既聯通內外,又著眼於虛實評價詩之美,不惟見歌者之靈心妙悟,亦展示了對現實的審美體悟,其守護和推闡儒家“溫柔敦厚”詩教的用心,同樣清晰。
總的看來,湯顯祖不僅重視情感於詩之基礎作用,也未曾放棄對儒家道義的追求。岳元聲《湯臨川玉茗堂絕句序》曰“詩,六經之微言也。騷人好譚詩矣,譚詩好譚微矣。好譚微而微絕,亦復更為不好譚微矣。譚其所不好譚微,而微更絕。微言不續,情性淆訛,而天地萬物之心閉。彼夫藉口雅言,而流連於鳥獸草木之騷屑者,此政不可與臨川言詩者也”,關聯“微言”“性情”論“玉茗堂詩”之隱喻,分析其道藝並重的詩學內涵,可以說是切中肯綮的。相反,大概是因為過分地強調湯顯祖的“至情”論,以往一些研究有意無意地輕忽了其詩學言說中的道義關切,這與其論詩的本意自是隔了一層。
(作者:溫世亮,系汕頭大學文學院教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 評論
- 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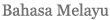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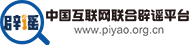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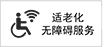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第一時間為您推送權威資訊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報道全球 傳播中國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
關注人民網,傳播正能量